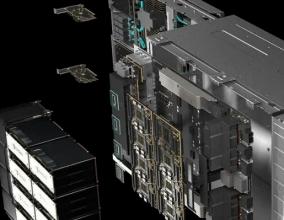对话传播巨头 在什么环境下看比看什么更重要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 时间:2003-06-18 03:23
主持人:本报记者吴晓燕 本期嘉宾:实力媒体副总裁郭志明
主持人: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中,人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C”上,即内容(Content)和渠道(Channel或所谓的媒介)。成千上万的研究者都致力于努力了解它们在传播领域的效应。但是相对而言,好像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了第三个“C”,即情境(Context)在传播中的作用?
郭志明:的确,在最典型的传播模式中,甚至从未使用过情境这个词。相反,“干扰(noise)”一词却经常出现。这就反映出了两点信息:(1)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元素;(2)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控制的。
主持人:但是“干扰”或“情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
郭志明:我们可以把情境定义为“传播活动所发生的环境”。
举例来说,如果一条广告讯息(内容)将通过电视(渠道)传达给女性受众,那么在它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其他广告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境。此时的情境还指受众的收视环境,包括电视信号的清晰度、受众所收看的节目类型,以及她们是在舒适的家中还是在嘈杂的饭馆收看等。
因此,情境涉及到许多因素。而且在营销人员的眼中,它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可控制的”。
主持人: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寻烦恼”探讨这个问题呢?
郭志明: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而且它是改善传播效果的潜在突破口。
主持人:到底“情境”的重要性在哪儿?
郭志明:在最畅销的《引爆趋势》(TheTippingPoint)一书中,作者Gladwell用了两章的内容对情境的效应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在书中解释了“破窗理论”的重要性。根据这种理论,如果一间房子的窗户破了没修,那么路人就会觉得这里没人管事。很快地,就会有更多窗户被打破,混乱和无序就会从这栋大楼蔓延到整条街,进而带来更多的犯罪。
事实上纽约市就成功利用这一理论降低了犯罪率。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只是简单地对地铁涂鸦、地铁逃票、公共场所醉酒、公共场所便溺等丑恶行为进行了整顿,就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该市的暴力犯罪降低了56%以上,而当时全国犯罪率的下降幅度平均为28%。正如前任市长朱利安尼(Giu?liani)在1998年对媒体的那次著名的讲话,“显然,凶杀与涂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罪行。但它们都是同一个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容忍其中一方也就等同于容忍了另一方。”
主持人:可以这么说,情境的重要性揭示出一个道理:微小的事情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
郭志明:对,想像一下,你在北京搭乘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空调坏了的夏利,恰好赶上7月的星期天,天气特别热。这时你在司机隔拦后面看到一则广告,试想这则广告会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主持人:到底怎样衡量“情境”的效果呢?它好像很难量化。
郭志明:尽管广告人经常抱怨难以衡量不同内容(广告)或渠道(媒介)的传播效果,但情境则是一个更难衡量的元素。它本身就极为复杂,而且很难加以量化。为了向营销人员提供可行的指导,多数研究者都只关注那些可能因某种原因而受影响或被选中的情境因素(如节目环境)。其他“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受众所处的传播环境)则几乎很少涉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关情境在电视传播中影响的调查结果:
长期以来,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两派之争。积极的一派通过对广告的回忆、态度或购买意向等指标的测量,证实观众对节目的参与越高,那么他们对广告的响应也就越大;消极的一派则正好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观众对节目的参与越高,那么他们对广告的响应就越低,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广告非常讨厌,并且会尽力避开它们(麦当劳,1995年)。
1994年,Norris和Colman试图为这种两难困境提供一个大概的解释。他们说之所以得到这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其原因至少可归结为两点。首先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原因。他们发现:对于高收视率的节目,当被调查者可以自由选择时,对他们的调查就会显示广告效果比较高;而当进行实验室研究时,得出的结果就会与此相反。其次,他们发现不同的预测变量似乎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们从过去的情境研究中提取出三项核心预测变量:(1)娱乐;(2)快乐;(3)参与。
Norris和Colman指出,多数情境研究者都会把这三个因素混淆在一起。他们的研究表明,节目的参与度越高,受众对广告的态度就越主观,越愿意购买;但他们对广告、产品和品牌的回忆度却越低。另一方面,节目的娱乐性和所带来的快乐与广告效果是无关的。
主持人:其他研究者从其他媒介,比如平面媒体来探索“情境”的影响吗?
郭志明:当然,例如,1998年Walker和Cardillo在英国针对“广告注释指标”对500人进行了直面采访,以试着对报纸广告的广告位置、尺寸和颜色产生的广告效果进行量化。他们发现,不同的因素(广告是刊载在前三版,还是刊载在右侧等)在不同类型的报纸(整版报纸和小开张报纸)中,产生的广告效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并没有研究文字内容情境的影响。
1995年Raimondi制作了了一个名为ROC(时机和说服力[RichnessinOccasionstoConvince])的指标,希望对情境在杂志广告中所产生
的效果进行量化。她从三个方面对ROC进行了定义:
?受众被广告感染、接受广告或拒绝回避广告的能力。
?与媒介相关的广告情境的吸引力,这取决于读者与杂志的关系,还要取决于杂志的广告内容。
?没有因为广告(广告过多或其综合情境太差)所引起的愤怒或厌倦。
但是结果远没有这么简单和直接。正如Raimondi所说:“广告的目标受众、杂志类型和产品类别之间的特别组合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广告效果:从非常受欢迎到令人难以接受两种广告结果都可能发生。”
一些国内的学者也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的陈红艳女士在一篇文章中从她个人观察的角度对情境产生的效果进行了讨论。她提到了在以下三种情形中,情境会对广告产生负面的影响:(1)当文字内容或节目情境与产品类别或广告内容不相干时;(2)当广告与其他类似或对立的广告一起投放时;(3)当广告形式不中看时,比如一个5秒广告与其他许多5秒广告一同投放在一个快速更换的广告时段中;或者互联网旗帜广告投放在颜色相近的情境网站上等。尽管上述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
主持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情境效果在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它对传播的影响机制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而且在近期内也很难对其效果进行量化。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郭志明:作为传播企划者,我们需要发掘情境的潜力,同时衡量其对营销结果的影响。
我们在三年前完成的一次成功的实验是诺基亚8250的“蓝色风暴”。其手机屏幕是蓝色的背景光。为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在目标杂志上刊登它的广告,而是成功地说服了选定的刊物,把他们的文字情境也换成了蓝色。对于喜欢这种颜色的目标受众,他们是很难错过这则广告的。此广告成为中国内地首次进入戛纳媒体金狮奖决赛圈的惟一作品。这一款手机也成为诺基亚中国公司历史上销量最好的款式之一。
另一方面,改变传播情境并不是增强广告效果的惟一途径。我们也可以考虑改变另外两个“C”,以迎合特定的情境。当情境超出营销人员的控制之内时,这一点尤为如此。
例如,在SARS传染初期,许多有远见的营销人员都在4、5月份疫情最严重时,改变了传播内容(讯息)或转换了渠道(媒介)。根据实力传播策略研究部门(SR)在5月初所作的调查显示,在这段时期人们的购买考虑因素和媒体习惯都发生了大的改变。例如,此时消费者把“杀菌能力”作为购买家用产品的首选因素。此外,他们开始更加关注电视和报纸。
尽管我们不能改变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境,但是可以主动积极调整内容或渠道,以增强整体传播效果。
在实力传播把提高客户的投资回报(ROI)作为核心工作之际,我们应当开始发掘情境在传播企划中的巨大潜力。
上一篇:脱离安全层高薪不胜寒
下一篇:华虹又推中国“芯”